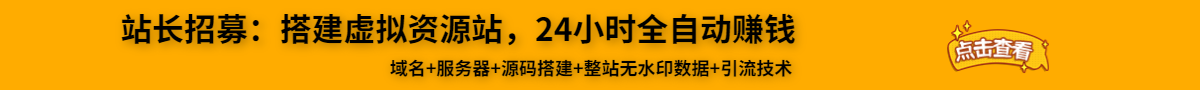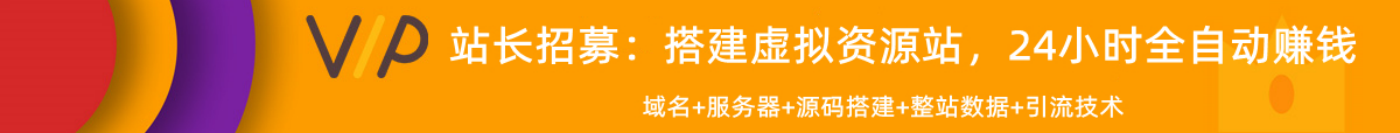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十八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在中国,有史以来,土地都是大问题。我自己懂事以后,就听说孙中山先生提出要“平均地权”,要“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通过种种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还知道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是对复兴中华具有关键意义的大事。后来知道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土地改革就是既定的国策。但在国民党方面看不到实施的意向;而在共产党方面,只知道在红色根据地实施了“打土豪、分田地”和“分田废债”的政策。进入解放区,又从文件里,从文艺演出中,知道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在农村停止了“分田废债”,改行“减租减息”。但这一切都只是知识的输入,离自己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
参加1946 年秋的土地改革,是自己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中国的农村。虽然这是一次右倾指导思想的“和平土改”,不能解决耕者有其田的要求,虽然自己的工作也浮光掠影地停留在表面,但确是自己对土地问题有所理解的开端。随后,由于纠正右倾而产生了严重的左倾,于是政策的掌握又从反“右”转向反“左”。这一段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反“右”反“左”的政策变换也时时推动自己思考,应该如何把握改革土地制度的方向。对于《中国土地法大纲》,我非常赞同,认定它就是在总结右倾倾向和左倾倾向并从而端正土地改革方向的《大纲》。所以当我第二次参加土改时三次土地改革的时间,在思想上的准备就是全面贯彻《大纲》的精神和做法。
然而,在我全心全意地按《大纲》精神开展工作时,有些原则、有些政策又不断向趋于宽缓的方向调整。如上面提到的对“平分”原则的贯彻更强调尊重中农的意见,如提高划成分的标准,如停止征收富农多余财产,等等。不久,在1948 年4 月1 日,也就是我还没有离开土地改革工作组的时候,毛主席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强调土改成就的同时也对纠正“左”的偏向给予肯定。实际上,趋于宽缓方向的调整,一直不断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任务的基本完成。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土地改革,已经是相当遥远的事情了。而在当时,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或者说,在直接参加和间接参加土改的这一代人还是社会主要部分的时候,还有许多不同的议论。像我这样跟着共产党走并且直接参加了土地改革的人,认定这是共产党的历史性的丰功伟业,并且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只能有这样的方针设计和具体政策措施。与土地改革没有直接联系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听到了不少土地改革里的问题,总认为是否应该走更为平和的路子。至于与农村有直接联系的人,有些人对土地改革持有保留意见,也有人,因为土地改革伤及其家人或亲戚,以致从支持共产党的立场转到对立面。在1949 年华北大学招收的近两万名政治班的同学里,大多数对土地改革都有着多多少少的疑问,以至不能不作为一个大的主题,安排时间,专门进行讨论。
我曾经认为,事隔多年,人们已经对那场土地改革极少提及了。不料,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些材料,反映了对这场改革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看来,问题还需要反复剖析。
就我自己的体会,土地改革直接的核心任务是实现耕者有其田;扩大到政治层面上讲,就是在农村里以劳动农民说了算来代替地主富农说了算的局面。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最为理想的途径应该贯彻打击面尽量小、团结面尽量大的准则。从实施的角度来说,这会使改革的阻力尽可能的小;就长远来说,在村子里更有利于形成长远和谐的氛围。其实,《五四指示》实际透露出这样的意向,比如,想依靠“献地”作为主要措施之一。但这很快证明行不通。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纠“右”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左”,于是又立即纠“左”。实际上,从纠“右”,到过“左”,到转而纠“左”,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整个过程仅仅发生在1947 年的前三个季度。如果说,纠“右”、过“左”,主要是在1947 年年中,而纠“左”的过程则持续多年,直到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大的社会变革过程好像有着自己的规律:反右会走向过“左”;上面走向偏“左”,下面会推向极“左”;而上面定下纠“左”方针,也并不等于“左”就立即纠正了三次土地改革的时间,这要克服下面极大的阻力。我体会,虽然自己从小一直接受和谐教育并总是下意识地追求和谐,这在当时叫作斗争性不强并经常受到批评,但在第二次参加土改这个大的社会变革里,也不时成为纠“左”的阻力。
在论证土地改革时,往往与地主阶级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联在一起,就像《白毛女》的故事那样。与我先后参加土改的同志们,有人就碰到过类似令人愤慨的情况。不过,在我直接接触的农村和听到一些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党员讲述,全国农村并不完全是一个样子。用现在已经很少用的语汇表达,那就是阶级矛盾有的尖锐,有的不那么尖锐。地主对于佃农,富农对于雇工,有的是强力压榨,不问死活,但大多的情况是地主也关注掌握租佃和雇佣的分寸以保持共存的态势——佃农、雇工活不下去,地主富农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不过,在当时,如果作有的地主心肠歹毒、有的地主心肠慈悲这种分析,那是犯大忌讳的;好像说地主都是心狠毒辣,才算立场坚定。有时联想到像《双城记》里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描述,好像在历史大转折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也非中国所独有。
要不要土改?在中国,历史形成的租佃土地制度,到了近代,已经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死结。只要中国不甘屈辱、落后、任人宰割,要走现代化的道路,那就必须工业化,相应地则必须有与大工业配套的大农业——当时通常的提法是农业机械化。进入20 世纪,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已经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但一个庞大的寄生的地主阶级,不可能有改进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佃农更没有力量改良耕作。当时的理论,实现机械化不外两个途径:资本的投入和小农的合作化。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走出了集体化从而机械化的实践道路更引起世人的关注。就中国的国情看,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把资本主义大农场看作是出路。至于合作化,或是集体化,则都是以革掉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前提。于是,“耕者有其田”,先使耕者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再寻求合作化、集体化、机械化的途径,必然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不能避开的纲领。不过,在解放战争打得硝烟四起,土地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这样“学究”气的论证,起不了鼓动作用。除了在华北联大这样的环境里有所探讨之外,就是在一般的干部圈子里也不可能深入讨论。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欢迎加入群聊
为了增进与粉丝们的互动,IMI财经观察建立了微信交流群,欢迎大家参与。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gxmw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