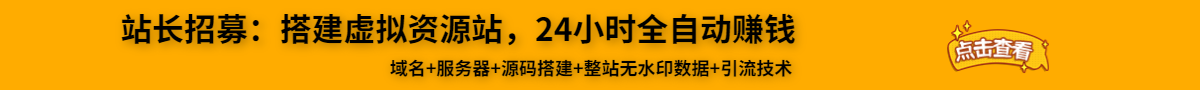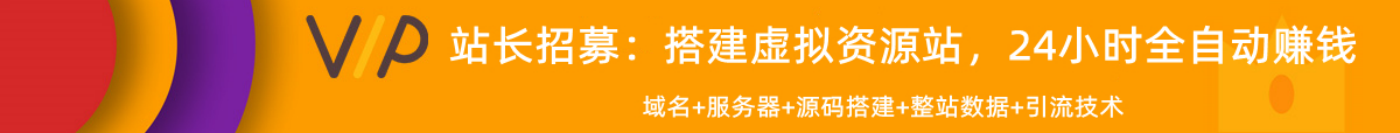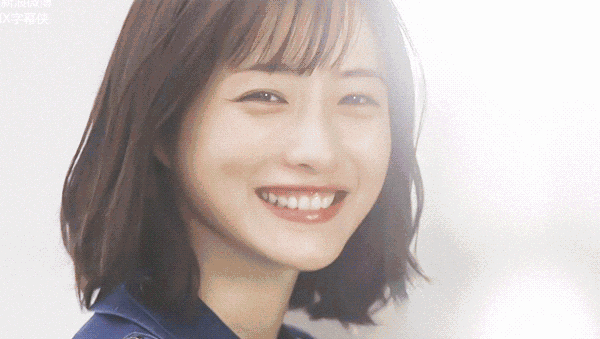导语
《水经注》大概是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中版本流传最为复杂的一种了。明清以来,无数优秀学者投身于《水经注》研究中,此学问迄今竟有“郦学”之称。郦道元何其幸哉!然而《水经注》一书究竟是如何写成的?既往学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往往笼统认为是郦道元亲身考察加其他途径撰成。然而最近的研究却显示,《水经注》很有可能是郦道元在“故纸堆”里检出来的。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文明社会,水是国家社会的命脉。水患之治,水利之用至关紧要。因此对于河流水体的记载在中国典籍上出现,得很早,很详细,甚至蔚为专门的篇章与著作,这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相比是一个显著的特色。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禹贡》,以大禹治水的叙事,记录了三十五条水道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战国秦代之际的《山经》虽然以记山为主,但仍然以山系水,详细记载了三百多条河流的分布,简略说明其源出、流向和归宿。而专门以河流为主要记述对象的文献恐怕要算《海内东经附篇》为最早,虽然篇幅很短,所记河流数量很少(仅二十六条),从地域范围来看,却是秦代主要河流分布相当全面的记载。故似可将其视作秦代水经(参见拙撰《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略论〈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的写作年代》,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到了汉代,出现长期统一疆土广袤的局面,于是《汉书·地理志》有条件记录西汉时期的三百多条河渠,成为当时河流水体最完整最全面的记载。《汉志》诸水的记载或系于源出地,或系于终结处,而且规模较大的水道,还载明了流经多少郡国。这么多的水道的基本要素如此清楚,说明西汉时期在中央已经保存有关于全国重要河流水道的基本资料。《汉志》是班固依照自己设计的体例,将西汉时期各类专项地理要素按政区体系割裂编排的结果,所以每条水道的记叙内容虽戋戋数语,其综合背景却是一个全国水系,其所据必定是当时已有的西汉境内水道的测量记录资料。由天水放马滩地图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关于此二出土地图的详细研究分别见:晏昌贵《甘肃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载《日本秦汉史研究》第十五号,2015年3月,该地图所复原出来的水道是甘肃秦岭西段南北的几条小河流,分别为渭水与嘉陵江的支流,地图时代为战国末秦王政八年;张修桂《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收入氏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我们可以看出实测的水道资料在地图上的显示。虽然这两幅地图所描绘的一些水道或许属“轻流细漾”,不足一提,或许未入班固所依据的史料之中,但《汉志》关于水道的记叙必定依赖于此类基础资料才能写成水经注作者,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且记载西汉时期全国水道的资料,显然比后来郦道元所注的《水经》还要丰富得多,因为后者所记也仅有一百三十来条水道而已。这也就是我推测在古代,水经所指不但是一部专书,可能还是一类书,撰写水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路由来(参见拙撰《中国古代撰写水经的传统》,载《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进而言之,东汉时期《说文》水部的记载,虽只记单名的水道,记述简略,但也具备出山、流向及归宿三要素。而且在《汉书·地理志》中未出现的马王堆地图中的深水,却在《说文》中见到,说明《说文》所据也是水经类型的资料,而将其分部别居,系之于相关文字的部首之下而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经则可肯定是成为专门著作了,但到底这个时期是只有一种水经,还是有多种不同的水经并存,则尚无定论。不过对郦注《水经》的复原工作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见黄学超《〈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李晓杰,2015年)。
在中国思想史上,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老子云:“上善若水。”孟子比喻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而在对现实世界的考察中,郦道元《水经注》对水也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自序一开头就说:“《易》称天一以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寓者,神莫与竝矣。”而在《河水注》中有“水德神明”的引语,又引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在《巨马水注》中又有“水德含和,变通在我”的述语,可以约略见到郦道元视水若神的思路。中国人重视水经的传统或许也与这些认识相关,还不止于实用的需要。郦道元所在的时代是魏晋玄学兴盛时期,虽然《水经注》是实学著作,但从以上《水经注》中的这些话,或许说明郦道元立意著述《水经注》时,未必不受到由道家与儒家融合的玄学的影响,虽然最终其成就却体现在地理学领域之中。

清代武英殿本《水经注》

《水经注》在清代得到了学者们的集体关注,许多人专心致志于《水经注》的研究。大名鼎鼎者如沈炳巽、赵一清、全祖望、戴震。他们争相以复原《水经注》的原貌为荣誉,甚而造成著名的“赵戴相袭案”。
《水经注》研究取径
《水经注》研究至少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文献学研究,必须尽量搜集现存齐备的版本,以进行文字校勘,使研究者先有一个可靠的最接近原本的本子可以使用。二是史源学研究,探知《水经注》文本的史源,尽量厘清编述与实勘的成份。三是地理学的研究,复原六朝时期的河流水道以及人文地理景观,编制出新时期的《水经注图》来,并且尽可能上溯下行,与古代的水文地理及后代的,乃至今天的水道系统作比较,以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地理环境的优化做出现实贡献。以上三方面研究是相互联系的,许多想当然的事,在深入研究中就会出现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水经注》的研究得到新的推进。而在实际上,尤其是从上述《水经注》成书过程的分析来看,对《水经注》的研究与其他传世文献相较,还有其特殊之处,即史源学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低于版本学研究。只有弄明白《水经注》的成书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找到其文本的源头,以促进下一步的研究。
在最新的《水经注》文本研究成果,即中华书局版的《水经注校证》卷二《河水注》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於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迳屈茨、乌夷、禅善入牢蘭海者也。”这最后一句的三个地名中,禅善(即今鄯善)至今仍在,屈茨即《汉书·西域传》之龟兹,即今库车,而乌夷到底指何处呢?单纯对照各版本《水经注》皆无法作出正解。当然,如果从释氏《西域记》本文去追寻,或许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惜道安所撰这本《西域记》已佚。但如果比照另一本传世的著作,就会明白,这“乌夷”之“乌”乃是“焉”字之误。章巽先生在研究《水经注》与法显《佛国记》关系时,摘出《水经注》里的另一段:“释法显自乌帝西南行,路中无人民,沙行艰难,所径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达于阗。”这其中的“乌帝”一语更是两字皆误,而究其实则为“焉耆”之讹(详见章巽《与》,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章先生引经据典,追源溯流,对比多种抄本刊本,详细考证“乌帝”致误的来源,令人钦服)。同理,上述“乌夷”也一样是传写之误。可惜《水经注校证》未注意到章先生这一早就发表的成果,而一仍其误。可见如果重视《水经注》的史源,以其所引用诸书来作深入探研,则对《水经注》本身的研究必定会有所促进。
郦道元写作《水经注》的秘密
许多现代的研究者认为,《水经注》主要是作者亲自踏勘调查所得的成果,因此在作者未亲自履历的地方,其记述就可能出现错误。这种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所以《四库全书》中的《水经注》提要说:“至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所未经,故于滦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阳之建置,俱不免附会乖错。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为传闻失实。”换言之,此语在客观上等于认定《水经注》是郦道元足迹所经处的实录与未经之处传闻的结合。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水经注》里确有郦氏亲自踏足之处,所以在书中他对几处实际地理情况与载籍记述之间的矛盾,做了合理的辨析。在引述他人著作时,也注意到该作者是否亲睹该水。但就全书份量而言,大部分内容是从相关的载籍摘取汇编而来,实勘的小部分主要多是因公旅行时所进行。业师谭其骧先生曾言:“古今有许多学者认为,全部《水经注》内容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词句外,便都是郦道元根据他自己调查、考察、研究所得写下来的,这是极大的误解。”又说:“郦注与班志一样,主要贡献也是在于郦道元纂集了大量的前人地理著作,而不是根据他自己亲见亲闻所记下来的那一小部分。”(谭其骧《序》,载《文物》1987年第7期,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所以《水经注》发生某些错误的原因主要并非因作者未作实地调查研究,而是征引典籍时出现的毛病,或误引,或张冠李戴,或随意附会所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条,举西汉安成、桃、建成等三侯国水经注作者,在《水经注》里皆两见为例。如同一安成侯,《赣水注》中定为长沙之安成,在《汝水注》中又说是汝南之安成。“皆彼此重复,不相检照。”),这一点实不必为尊者讳。

有学者认为郦道元自序中“访渎搜渠”四字,是亲自踏勘的意思,其实不然。这里的“访渎搜渠”必须要从上下文语境来进行综合考索。郦道元在自序中早已表明他自己“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他所做的主要大事,是将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著作里的地理材料,按照河流水道的分布,一一安插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建构成一个新的地理体系。这种创造性贡献的特点,简而言之,或许可如古人所总结的所谓“因水证地,即地存古”。这个工作貌似纸上谈兵,却是在学术领域做了一个崭新的贡献。而所谓“访渎搜渠”四字是要放在“辄述《水经》,布广前文。……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的大语境中去体会的,也就是说,道元先以《水经》为骨架(“辄述《水经》”),再将前人之文(“前文”)加以演绎(“布广”),将从前人书籍中访来的渎,搜到的渠按照枝流吐纳关系,以及水流沿路的相关各类地理资料,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系统。
事实上,要将载籍中“乱流而摄诡号”、“直绝而生通称”的河流名号分辨清楚,并且将“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的水道体系整理清楚,并在文字上清晰表现出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郦道元做到了。他将大小一千多条河流一一梳理清楚,安排妥贴,尤其是要将河流的各级支流都叙述到(漳水并不算长,却连四级支流都涉及了),而又不能错乱,真是太难了。之所以要“访渎搜渠”,其意义端在于此。所以他坦白承认其著作的出现是因为空闲时间太多,担心虚度了年华,所以才拿《水经》来消遣,将“前文”加以“布广”,而结果却衍绎为一本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如果他前文自己已经说过对“寻山”与“问津”并无兴趣,而后面又说“访渎搜渠”是亲力亲为,那岂不是一个大矛盾?
陈桥驿先生曾总结说:“郦氏撰述《水经注》,其方法从实地查勘、稽核地图、引征文献以至访问外国使节”而来(陈桥驿《水经浿水篇笺校》,《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这样说自然很全面。然究其实,征引文献实占其中的大部分。而古人在征引前人文字时,又为行文之流畅可读,往往不具引书名作者,甚至有时只概述引书的大意(这其实不独郦氏为然),使得后人以为《水经注》中除注明出处外,全书大部分为郦氏所著,于是有时就会对文本产生误读现象,以至对郦道元以北朝之臣而行文竟用南朝年号的情况曲为之解,认为道元有大一统思想(陈桥驿《郦道元评传》,第37-42页),这就未免有点谬托知己了。其实郦氏不过因为直接摘用南朝人的文章,自然不改其年号。更有甚者,《江水注》中还有实指宋文帝的“今上”一词出现,岂非更大逆不道?其实这一点也早已由顾炎武《日知录》“引古必用原文”条所揭示: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州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増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也就是说,作文时引用前人的文字必定要用原文,并非郦道元出了毛病。包含“今上”在内的一段文字是从盛弘之《荆州记》照抄来的,并未因郦氏仕于北朝而改称南朝的“今上”为夷酋之类。又,时南北朝对立,南朝詈北朝为索虏,北朝则蔑南朝为岛夷。
事实上,郦道元的喜欢读书,早见于史载。《北史》本传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自《水经注》行世以来,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水经注》就已以征引文献之丰富,为学者所瞩目。明代朱谋㙔《水经注笺》对征引典籍已作部分溯源考订,现代学者郑德坤更详细考证出明引的典籍有436种(见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厦大图书馆报》1935年第2、3期,但436种之数在前一年的《水经注引得·序》中已揭示。陈桥驿则以为有477种,不过陈先生计数法略有不同,如《山海经》通常以一书计,而陈先生将其中之篇目如《山经》等复计为另一书)。但是现有研究清理《水经注》征引文献数目,均以明确标注书名、撰者为限,对传统撰著方式中引而未注、撮取文意的征引(或可称“暗引”)则未能全面揭示。如果再认真追寻其暗引的典籍,并大致估计其份量,更可清楚看出《水经注》的基本内容应该都是来自六朝及其以前诸相关文献。
有鉴于此,我建议复旦大学的夏婧博士后,从文献学角度就《水经注》的暗引成份进行了探究。事实上,暗引材料若不仔细甄别,实难以确知。“如陈桥驿指出郦书引称《法显传》仅八次,所计显然以文中明确标出‘释法显曰’、‘法显传曰’为据。而比对《法显传》,可进一步判定卷一《河水》大半篇幅均出其书。”(夏婧博士后出站报告《援引文献溯源研究》第9页)又“如卷三七《夷水》篇内基本没有标示征引书名,偶有一两处提及‘盛弘之以是推之’,‘袁山松云’,借助唐宋类书保存的文献片段,可以确定通篇几乎全部采自盛氏《荆州记》、袁氏《宜都山川记》、《荆州图副》等典籍;又如卷三六《沫水》,从逐条内容推证,也可判断相关叙述皆本于常璩《华阳国志》、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同上)
进一步研究,则会想到,郦道元引用典籍数量甚巨,一方面有检索之难,另一方面,这些书是否都唾手可得?因此会不会有间接辗转引用的可能?也就是引用类书或其他现成的注书,如《史记集解》之类?经过考证,可以知道“郦注对传世典籍的援引,往往存在辗转他途的现象,比如最大限度地参考借鉴某书已有的集注、集解本。一些生僻或稀见文献的获得可能即出此法。进而言之,注释中某些错误观点的形成、材料引文与通行版本间的文句差异,或许也与这些隐性文本的存在有关。”(同上)此外,郦注未标举引书来源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出于汇考群说,或者拼合同一书不同章节叙述的征引方式等等情况。
要之,根据李晓杰等人对汾水与渭水诸篇的史源学研究与夏婧对全书的抽检(关于《水经注》史源学的研究,近年来也有其他学者加以留意,如鲍远航博士论文《文献学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第二章专论《水经注》暗引的问题),《水经注》全书是以征引同时及前代典籍为主要成份,而不是以个人的实地考察为主要依据,是完全可以断言的。

本文乃周振鹤先生为《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一书所写序言节选,原文已刊于《文汇学人》2016年12月23日。该书亦已于2017年1月出版。
暨南大学舆地学会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gxmw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