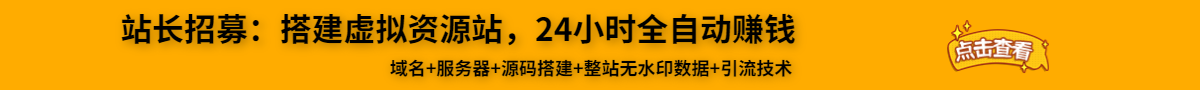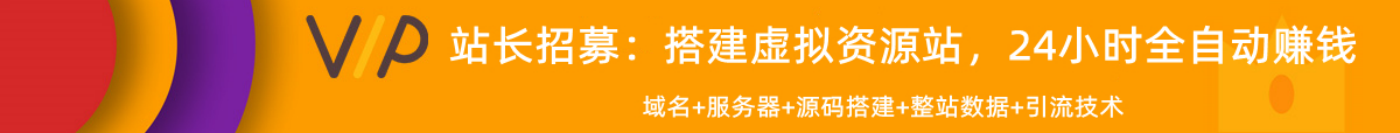【福建生产建设兵团题材长篇小说】
落入金河的杉树果(第十五章)
郭瑞明 著
十五 告鸡奸批斗小战士 写墓碑悲戚刘金铭
这天是星期天,大伙放假休息,陆陆续续都到集镇上赶圩去了。刘金铭到值班室看看是否有自己的信件。上次收到林素梅的来信让他高兴了好几天,把那信翻来覆去读了又读,看了又看。今天又收到她的来信。
林素梅在信上说,她是怎样知道他的单位和地址的,这个要留着等以后见面再说,当面说才有意思,刘金铭看她又卖关子,读着不禁笑了起来。林素梅告诉他,自己在劳改监狱看押犯人,还是荷枪实弹的,有机会到她单位去,要带他去看看她的自动步枪和看管的犯人。她在信里叮嘱刘金铭上山砍树要特别注意安全,不要过分劳累,如果有时间画画,无论好坏都要留给她看。她也准备开始画画了,一定要把那幅梅花画到自己满意为止,当然也希望他能够教她,多多去信帮助她提高。林素梅在信里面夹上一张半身照片,她说这是偷拿他爸爸的军装去照相馆拍的,之后被知道了挨了老爹一顿臭骂。
这是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照片,右下角印有“红旗照相馆”的字样,不愧是省城的照相馆,照片让人的感觉质量很不一样,照相师的摄影水平也很高:照片上的林素梅,虽是军帽军服,一副女兵的标准做派,但难掩其俊俏靓丽,自信满满,光彩照人。她的眼睛大而有神,眸子里似乎有清波荡漾,直视着你仿佛能看穿你的心思;两道修长的眉毛直逼鬓角,之间那点淡红色的痣格外的引人注目,平添了几分俏丽,看起来又庄重大气。既有亲和力又有种距离感,若即若离的感觉更加的吸引人的目光。坚毅挺直的鼻梁,兼有女性的俏美又有点男性才有的英气;嘴唇略薄给人以柔软、细润的感觉仿佛欲说还休似的;在刘金铭看来,有军帽上红五星和衣领上两面红旗的威武衬托,更显得她是那样秀雅绝俗,神态悠闲、美目流盼、含辞未吐、气若幽兰,自有一股轻灵之气。
这就是林素梅!——刘金铭想起那晚在无名小站上,第一次看见林素梅身披军大衣在路灯金黄的逆光下款款走来时,心灵的被冲击被震撼的感觉,这种被唤醒对女性的感受虽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可仍不是那么的明了依旧还像是在朦胧之中,像是被飘渺云雾笼罩着的神女峰,你能看出她的身姿却看不清她的容貌,在你的满足中偏偏留给你很大的缺憾,这样更让他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致命的向往。那天晚上,他们之间说了那么多话,谈得那么投机,似乎都还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刘金铭只觉得她漂亮漂亮漂亮,但始终不敢直视她脸部一眼。尽管那愿望如此的强烈,直到分手,他只记得她说话的声音、语气和她远去的身影。她转身而去留下的一丝清新的特有的神秘而诱人的气息,至今紧紧地笼罩着他,那种神秘已经将他的心牢牢地拴着……
现在,刘金铭可以捧着她的照片,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把她看个够了。看到发呆为止,甚至还很罗曼蒂克地想象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对话。可是他一想到她有个部队的老爹,心里有点发怵,但是又转念一想,我们就是革命战友之间写写信,有啥好说的呢?原来自己和杨秀蓉不是也来往得很好吗?她爹大小也是个干部,但是现在被批判被打倒了,说是历史反革命,尽管是这样,他的心里对杨秀蓉这个反革命子女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尽力为她能够参加兵团向带兵的张干事极力推荐,更为她能够如愿和自己一样成为兵团的一员感到十分开心。他在心里从来就认为,同学之间的来往,和大人有什么关系呢?
杨秀蓉两个酒窝的笑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她的来信比林素梅要迟得多,尽管都同在一个团都同在泰化县境内,但是交通的不便往往影响到通讯,要收到一封信也是要几天的时间。
杨秀蓉的信里说的是她们连队里的事情,那么多的木材全部泡在河水里面,用竹钉和篾笍绳装订成一连连的木排,捎排工人驾驭着由水路放流到顺昌,想象着操纵那么长长的排捎,在葱翠的群山里沿着蜿蜒的河流穿行,虽然很艰苦也很危险,但还算得上是很浪漫很有诗意的事情。要是我们能够白天在一起操纵一连木排,穿越金河的碧波;晚上就住在厂排上,一边煮饭一边欣赏金河的暮色,肯定能够合写出一首动听的放排歌来,你信吗?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宣传队一起创作过节目,可是那些都是无病呻吟故作高尚,只有这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写出来才是有意义的作品。
刘金铭想到自己已经磨出厚厚老茧的双手,红肿破皮流血结痂的肩膀,对于杨秀蓉的天真烂漫,想要回信告诉她,在我们森工林业,没有一行是轻松的,你在行外的角度看得轻松浪漫,其实都很繁重很痛苦很单调,只有你身在其中以此为业,一开始你就会尝到真正的滋味,才会真正理解它的内涵和意义。生活中有浪漫当然很好,但是浪漫往往会被严酷的现实一点一点地磨掉,最后被无情地摧垮。怎么会这样说呢?太沉重了吧?
刘金铭摊开信纸,拿出钢笔,想给林素梅和杨秀蓉各写一封信,想想禁不住又拿出林素梅的照片来,在信纸上用钢笔勾勒起林素梅的头像来。
陈勇志不知道啥时候从哪里冒出来:“金铭,有信纸两张给我吧,我想给老婆写封信。”
刘金铭头也不回地撕下几张信纸:“前天你不是刚刚寄出去,今天又写啦?”
陈勇志凑上来一看:“哈哈哈,现在不看那个铁罐子专看照片啦?呀呀呀,真不赖呀!跟对象谈恋爱了?照片给我看看行吧?”
刘金铭说:“不行!什么对象?什么恋爱?没有这回事,都是革命同志。”
陈勇志说:“前两天在那一棵百年的老杉树上,我采到了两个连在一起的杉塔,你要不要呀?”说完把手举得高高的——两个杉树果下半部紧紧长成连体,成为V字型。
刘金铭瞪着眼睛看了看,猛地跳起来:“给我给我——”蹦了两下够不着陈勇志的手举得高。
“你的铁罐子里头收的杉树果,都没我这个的稀罕。”陈勇志故意逗他。
刘金铭眼盯着那颗连体杉树果:“说吧!我拿啥跟你换这个?”
陈勇志眯眯地笑着说:“不用换,只要你告诉我这要送给谁?代表个啥意思?我就给你!”
刘金铭涨红了脸:“我自个喜欢收藏这个,没想送给谁的。”
陈勇志瞟一眼刘金铭身边的照片,意味深长地说:“行!好好藏在铁罐里面,放在铁罐里面就行,这女同胞是真当兵的吗?好漂亮,哈哈哈。哎哟——眉心有一颗痣,这可是大富大贵之人,今后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啧啧啧——”
刘金铭拿过那个并蒂的杉树果,在身上擦了擦,又放在嘴边吹了吹,打开那个麦乳精铁罐的盖子放了进去:“你可别乱说!我要送给她也是革命同志的友谊。”
陈勇志更大声的笑起来:“得!什么革命同志的友谊?你这个劲头,早就让她把你的小命給革掉了吧!”
刘金铭赶紧递过几个信封和几张信纸:“好好好,谢谢你给我这么个好东西,改天进城里我请你吃肉片汤面。”
“行!”陈勇志拍拍刘金铭的肩膀:“下次我还帮你采。”
刘金铭打开铁罐子说:“这样的有一个就够了,你再采到的,拿回去送你老婆吧!”
陈勇志说:“看看看看!这东西是要送给谁的?你这是不打自招了吧?你还忙啥?我们一起去赶圩吧,农民卖的土产可多呢,笋干和红菇,最好。”
刘金铭合上盖子:“我不想去,你替我买一块钱鸡蛋吧。”
“我听他们讲赶圩一块钱能买十个鸡蛋,遇上个好说话的还给十一二个呢!我想去看看笋干和香菇,这东西这里便宜我们那边金贵。你不去我走了”
陈勇志风风火火的大踏步走了,宿舍里没几个人,各闲各的。刘金铭把几封来信又看了一遍,心里琢磨一番,提起笔来,先开始给家里爸妈写信,写着写着,又想到该洗衣服和被子,怕等会又忘记,停下笔来,先把要洗的衣服,还把被子拿出拆开,胡乱放了一床铺。
这时候门外走进来一个人,约摸五十开外,是个五短身材个头不高,但是很壮实的汉子,平头短发,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建设兵团是什么意思,上身穿着一件军色绒衣,露出里边的白色衬衫衣领,下身穿着一件宽大的军裤。他就像到了自己的地方一样,进来后很随意地四下看看,问刘金铭:“今天休息,给家里写信吗?”
刘金铭看了他一眼,一时不知道他是谁,心里猜想可能是临时来连里的什么干部吧,漫不经心回应了一声:“是,写信给家里。”
“对,应该经常给家里写信,让家里人放心。”这位壮汉带着鼓励的口气说,他指着陈勇志的床铺问:“你对床的战友是复退军人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刘金铭心里十分惊奇,赶忙站了起来看着他。
“哈哈,小战士,我看他叠的被子就知道他是一个兵。”
刘金铭看着自己的床和自己身上穿的旧衣服,感到十分狼狈,手脚无处安放。
壮汉把刘金铭上下打量了一番,走上前握着他的手,用另一只手在他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两下,笑呵呵地说:“小油条!”随后迈着稳健的步子一边左右看看一边往外面走去。
刘金铭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那壮汉坚实的身影消失在门外。他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壮汉,别看他和和气气,言语不多,但是身上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含而不露的威严和气场,举手投足之间那种稳健大气和坚定自信。那种无形中让人敬畏是他所见过的大小干部所根本无法具备的。
不一会他回过神来,心里一激灵,赶紧追到门外向办公楼下看去,看到有几个人拥簇着那位壮汉,其中好几个是军人,还有两名挎枪的战士,走到办公楼前的空地上,这时只见小七星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两个人跑得气喘吁吁来到壮汉的面前,双双“啪”地立正行了个军礼,壮汉对他俩摆了摆手,一行人边走边说着什么,转到办公楼后面去了。
刘金铭想,这人到底是谁呀?他拿出衣服和被单到食堂后面的水槽,用肥皂粉泡在脸盆里,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是大首长下连看看,具体的不知道是谁。
是不是上面来人处理“鸡奸”的事了?他想起上周发生的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睡在四排长旁边的吴玉辉那天向连部告状,说四排长鸡奸他。这事可闹大了,都在私下议论纷纷。这天指导员亲自坐镇,开了一个全连男战士参加的批斗会,说是吴玉辉诬陷四排长。好家伙,只见几个膀大腰圆的退伍军人把那小吴推进会场,喝令要他跪下,见他不跪,马上就给他一顿拳打脚踢,强按着他跪下,吴玉辉摔倒在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涨红着脸大声抗议:“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指导员看着几个复退军人合伙揪人打人,竟然默许一声不吭。
这时九班战士魏晋文实在看不下去,就站了起来,说:“不要打人。即使小吴有错,但他也不是阶级敌人。他可能不知道鸡奸是什么意思。”魏晋文也是个老三届高中生建设兵团是什么意思,在连队算是见多识广,平时说话也有分量。吴玉辉望着魏晋文,显然是希望他能说清楚。魏晋文接着说:“我们通铺一个个挨着睡在一起,晚上睡得糊里糊涂,搂抱在一起,是很正常的,这不叫‘鸡奸’。只要四排长的生殖器没有进入你的肛门,就不能说四排长鸡奸你。”
魏晋文说得有条有理,但不知为什么,许多人哄笑起来,指导员忍不住也笑了。刘金铭和另一个战士同时站起来想发言,刘金铭抢先说:“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认为不能这样对待吴玉辉同志!”
那位战士接着说:“鸡奸是错误的!要道歉要接受处分!”
四排长站起来说:“什么‘鸡奸’?胡说八道!我还要说是他吴玉辉鸡奸我——”
那帮退伍兵在一旁起哄:“谁看到了鸡奸呀?拿证据来呀!没证据就是胡说!”
吴玉辉气的脸色发白,浑身颤抖,他很不服气地大喊:“你等着!我还要去告你!”。几个动手打人的幸灾乐祸地看着他。谁都知道四排长平时和指导员的关系很好,和那些个复退军人有事没事的总混在一起。
这时二排长举着《毛主席语录》站起来说:“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认为这事还要深入调查清楚,到底是诬陷还是误会什么的,再做结论。但是开这样批斗会我看不合适!” 开会的人大部分默默地观望着,那些积极发言的基本上分成了两拨,都抢先念着最高指示为依据争论来争论去,几个老工人、刘金铭也是和魏晋文的意见一致,极力地反对这种粗暴对待战友同志的做法。最后指导员悻悻地说,好吧!这事要反映给上级处理。
散会时,两拨人嘴里都骂骂咧咧地,心里谁都不服气。刘金铭在心里也是堵得慌。
中午陈勇志赶圩回来了,问刘金铭:“今天上午彭司令来我们连了,你见到了吗?”
“彭司令?哪个彭司令?”
“看看你就知道你这没真正当过兵的。他是咱们兵团的彭司令彭将军!”
“是吗?哎呀——我真不知道呀!他来看见我写信,跟我握手,还叫我‘小油条’!”
“你向他立正敬礼说首长好了吗?”
“我不会呀,我都傻傻的,到后来还搞不懂连长指导员为什么向他立正敬礼。他看到你叠的被子还夸奖你才是个兵。”
“呸呸呸!首长跟你握的手白握了——后悔死了,早知道我就不去赶圩!和彭司令握手的应该是我!”陈勇志一个劲拍着脑袋懊悔。
刘金铭这才知道,跟他握手的那位壮汉是我们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彭飞。他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呵!他真是后悔死了,傻傻的不会立正向彭司令行个军礼,不懂得问一声“首长好!”。他下意识地看着自己和彭司令握过的那只手,他心里要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家里,告诉林素梅自己是“小油条”,还要告诉杨秀蓉。
刘金铭问陈勇志:“彭司令来咱们连干嘛了?处理那鸡奸的事情吗?”
“那样的破事值得司令来处理?你也真是的。他们领导的事情,用不着我们去打听。有命令我们执行就是。”
“鸡奸是小事情吗?”刘金铭不解地问:“还有那样打人行吗?”
陈勇志一时语塞,讪讪地拿出买来的鸡蛋,两人正说着赶圩的事情,老牛头进门来说:“小刘,连长叫你过去一下。”
刘金铭问:“啥事呀?马上去吗?”
老牛头说:“马上。连长还问你要不要带毛笔?还是粉笔?”
陈勇志说:“又要写新的最高指示?”
老牛头说:“不是,给七班那大李和黄祥志写墓碑。我到县里找人用石板刻墓碑又贵又麻烦。连长叫人用水泥模了两块墓碑,现在半干了,说你的字写得好,要你在上面刻字,趁着水泥还没干,干了就没法刻字了。单用红油漆写不行,没半年就看不清字。”
刘金铭说:“那天开他们俩的追悼会,我跟大伙都哭了,心里头难受了好几天。好端端的工友,钢丝绳打下来人就没了,我到现在好像还听得到两个大嫂和孩子的哭声。一说起来真难受。还不知道我手会不会发抖?好,我们去吧。”
他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外,在路旁捡起一支竹片,用刀削薄削尖,对老牛头说咱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办公室后面的空地上,看到冯连长、林指导员阴沉着脸,汪副连长、季副连长和七班长、老刘、小范都在那里小声说着话。他们面前地上放着两个薄木板钉成的木槽,约有一米半长半米来宽,槽里边铺着塑料薄膜,木槽里面灌满灰水泥,表面抹平得光光亮亮。
被绞盘机断落的钢索击中伤到头部的大李和腰背受伤的黄祥志,在紧急送往县城医院的途中,运送他们的解放CA-10卡车和风风火火赶来的救护车相遇,医生急忙下车,被卡车上的人使劲拉着费力地爬上后厢板,先后摸摸两个病人的颈动脉,试试鼻孔的气息,睁开眼皮仔细看看,然后摇摇头对车上的人说:“瞳孔放得很大了,完全没呼吸。送医院没用,拉回去吧!”
大李嫂和黄嫂一听立马放声大哭,凄惨的哭叫嘶哑狂咽抽泣让身边的人不忍听。
七班长立刻大声叫了起来:“不行!要送医院!送医院就会有救的!”
医生站起来往车后厢板要跳下去:“同志,我们这是遵照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呀!”
七班老刘急红了脸用力扯住医生的领子:“你什么主义?什么主义?赶紧拉去医院抢救,别废话!”
七班小范:“妈勒个鸡巴子!人要死了还不救?你不救等会我叫你一起躺着去医院抢救!”
汪副连长和季副连长站在车后,不断摇手示意叫老刘和小范先别说话,一个人各伸出一只手把医生扶下车来,医生下地踉跄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歪了一边。
汪副连长说:“医生,让你辛苦了!工人弟兄心急说话冲,你先别见怪。”
医生站稳后看他是领导模样,一脸的委屈,把听诊器收好放入衣袋,不吭声。
汪副连长接着说:“我们工人阶级也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设备出了问题,造成这么大的工伤,大家都很心急,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医院尽力抢救!”
季副连长说:“医生,我们场现在是解放军兵团的了,全国不都要拥军学习解放军么?我们解放军首长领导很重视安全生产,一会都会亲自来过问的,你就大力支持吧!”
汪副连长心急地说:“医生,时间紧急,我看赶紧把病人抬到救护车上送医院。剩下的问题,让我们部队领导和你们院长去处理吧?”
医生说:“好,你们赶紧把病人抬到救护车上,动作要轻一点!”
救护车和解放CA-10卡车一前一后开着大灯按着喇叭,风一般地朝医院开去。
伤重的大李和黄祥志终是没能救活,死了。
尸体拉回小七星伐木场他们生前为之劳作的地方,家属哭的死去活来,同事黯然神伤。
追悼会开过了,下葬了,这就等着这两方水泥板墓碑各自刻上他俩的姓名、籍贯和生卒年月。
汪副连长拿出一张纸,拿给刘金铭看:“这是墓碑上要刻的字。墓碑上方都给他们刻上一个五角星吧!做一个标记,好歹也算是咱建设兵团的战士。”
水泥板已经半干,刘金铭掏出刀状的竹片划下去,出现一道边界凌厉的划痕,就像医生的手术刀片剖开僵硬的尸体,没有血流出来。面对那两个名字他觉得自己的手止不住地发抖,只好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地让自己心里平静。
两位死去的战友虽然不同一个班,尽管交集不多,毕竟是同一个连队的战友,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刘金铭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将他俩和眼前这块冰冷乌黑的墓碑融合在一起。在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这里的每个人离死亡都那么的近,近得就像他面对着这块将要凝固的墓碑,死亡发出的水泥的腥刺味道,从鼻孔直冲脑中,让他感觉有点眩晕。
用竹刀模仿毛笔的运笔,无论他怎样用心,刻出来的字样很不流畅,显得非常的笨拙,好像一个人的心事太过淤积堵塞,表达出来的就是结结巴巴的难以成句。
几天以后,在小七星伐木场后面荒野的坡上,两座并排的新坟墓前各竖着一块水泥板的墓碑,上边的五星和文字是在水泥半干的时候用竹刀深深的刻进去的,刘金铭用竹刀代笔,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思,按照毛笔楷书的结体和笔法,一刀一刀很认真地划上去。墓碑上凹进去的五角星和文字是用红油漆描上的,格外的刺目。通常表示喜庆的红色,在这里却因为与死亡的关联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仿佛那些腥红色是快要滴落下来的血液,心中不由得涌起恐惧和哀伤。
风寂寞地吹过荒野坡上的杉树林,越刮越猛,杉浪涛涛,相邻的松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松涛滚滚。突然可听到哗哗啦啦、铿铿锵锵、霹霹啪啪、悉悉簌簌,犹如被惊扰的猫头鹰噗噗的飞起,石片跌落碎裂;也如被惊动的野兽嗖嗖地逃窜,枝桠摇落叶草纷披;风声远去又低回,更像是人在叹息,又像是哭泣,更像是好几个哀怨妇人悲戚的啼叫。
一阵旋风卷过墓前的空地,落叶和杂草打着圈圈转起来,没有烧尽的纸钱带着灰烬跃升到半空中飞旋,像灰白蝴蝶一样地起舞,在空中划出的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怪异轨迹,像是在挥写着什么隐晦的咒语。花圈上的白纸条被风扯断刮上了天空,飞得不知去向。
墓前的花圈被风刮倒在地,竹条编扎的圈子散开,捆扎在上边的松枝杉树枝叶掉落一地。墓碑前砖砌的小案桌上,酒杯、烟支、果品还有酒瓶满地乱滚。
杉树上的杉树果、松树上的松果在狂风中纷纷坠落到满是枯枝败叶的地上,果实上的鳞片将会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地张开,种子会从草根的缝隙里落入泥土,开始了它们生命轮回的另一个历程。
风停了,一切重归于沉寂。如果没看到这些散乱的痕迹,没人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发生过。该发生的发生了,该过去的过去了。
小七星伐木场上班的哨子声依旧吹响,战士们肩扛手提工具,穿过荒野爬过山岗,出入密林之中,绞盘机的钢索重又横跨在空中,沉重的木材被轻轻地吊起送到远处山那边的堆头。油锯的声响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吼声传遍山谷,“嗨呦嗨呦”挑筒的号子回荡在密林之间,粗犷低沉浑厚的嗓音,带着强烈节奏的半喊半唱:
“弯下腰啰!”“嗨哟!——”
“稳上肩啰!”“嗨哟——”
“直起腰啰!”“嗨哟——”
“起步走啰!”“嗨哟——”
“顺直放啰!”“嗨哟——”
“超额完成第一季度任务”和“大干红五月”的口号响亮地提出来,热气腾腾的氛围被营造出来,并实施一大堆的具体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增产再增产的高度目标。在一场明亮刺眼灼热逼人的气浪掀起卷来的时候,你只能跟着走,无暇顾及其他,看不到有暗处的东西。
刘金铭和一班的战友们经过那片荒野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都要转头望望远处的那两座坟墓,那刺目的红色五角星和碑上的几排描红文字,淡化在遥远的距离和浓重飘忽斑驳色彩的背景里面。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字,不是文学艺术的内容,不是镌刻在展示书法艺术的场合,而是陪伴这不幸离世的战友竖立在这荒野之中。
难道为生命的不幸的涅槃而书写,也是艺术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两位原是七班的战士,刘金铭和他们没有什么交集,倒是大李这位山东的汉子,有次急着要往菏泽老家写信恰好文书没空,听说刘金铭写字写的很好,来到他的面前小心地问能不能帮写封信。当时刘金铭痛快答应了,还嫌他的信纸信封不好看,用了自己的信纸信封,这让大李很是感激,写好以后就以他的大嗓门逢人夸奖刘金铭。
也是那次写信,刘金铭才知道大李还是老兵,曾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据说当时还代理过副排长,可惜的是没文化一字不识,退伍以后回到原籍,正好福建开发山区林业,山东政府需要调配一批人力,于是他就应召转到福建林业部门的伐木场来了。小七星伐木场还有一群像大李这样的老工人。
1958年,为了解决山东地方工业各项基建工程需要木材的困难,鲁、闽两省省委书记舒同和叶飞在华东协作会议上商定了两省人和物交流、互相协作的协议,由山东组织两万多劳动力支援福建林区开发,福建则支持山东木材二十万立方米,毛竹二十多万根等林木物资,合作期限为一年半。
山东省委根据两省协议精神,在济宁、昌潜、莱阳、惠民、临沂、聊城、荷泽等地动员两万二千名壮工南下福建,加入木材采伐行业,其中单聊城一地就有二千名壮工,当时分配莘县、范县二县各五百名。征召的工人其工资、福利待遇、伤亡病残处理,按福建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1958年,大跃进运动展开后,全省在短时间内办起235个伐木场及一批贮木场、水运队、采购站、运木车队、林业工程队等森林工业企业,森林工业职工猛增到10万多人。另有社队采育场(队)570个,专业劳动力4万人。三溪市、南延市是福建省的重点林区。
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鲁、闽两省合作的期限已到。福建省林业厅领导向省里汇报称:这批南下的山东工人已成为林业生产中骨干,又都是强劳力,如果调回山东对整个木材生产影响很大,在华东开会时山东省政府负责同志商讨后,同意不回山东的可留在福建工作,后来定下了个文件:去留自愿,留下的同意把工人家属分批迁来福建,落下户口,原先的工人一年半转为正式国营工。所以1960年开始留下的工人陆续从山东接来家属,在福建三溪林业系统开始一种新生活。
1960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决定,安排山东籍林业工人家属4万多人来福建。在荒山野岭的茂密原始森林中,路隘林深,粗笨的挑筒杆和手锯砍刀,没有机械设备,伐木工们用血肉之躯铸造开拓了闽省的森林工业。
“抬起来呀,嗨嚆!齐步走啊,嗨嚆……!”撼人心魄的劳动号子回响在闽山碧水密林之间,山东口音的呼唤和大葱烙饼的气息久久回荡。
大李的身世和遭遇,让刘金铭怎样也忘不掉大李求他写信时虔诚谦卑的语气、浓重的山东腔话语,还有十分热情执意要送给他的烙饼和大葱。
如今他再也不用托人写信回家了。
刘金铭刻上去的那些字为这位山东汉子的一生写下了一个句号。(未完待续)

1973年冬 作者在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团团部
作者简介
郭瑞明,厦门同安人,马来西亚归侨。退休前任厦门《同声报》[CN35(Q)—0051]主编等职。系厦门作家协会会员、厦门书法家协会会员、厦门楹联学会会员、厦门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著有:《厦门人物(海外篇)》(1996年 鹭江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版);《厦门侨乡》(1998年 鹭江出版社出版,2002年再版);《同安华侨史略》(2012年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出版);《同安境外宗乡社团概略》(2018年鹭江出版社)等;
作者于1970年1月应征加入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先后任职于第十团宣传股、第十团文艺宣传队、第二师文艺宣传队、第十一团文艺宣传队、第十一团电影队, 直至1975年5月转入地方工作。
创作有:
视频片《回望芳华——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50周年大会宣传片》;
视频片《永怀芳华——福建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伍》;
美篇《全国首座兵团亭——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纪念亭》等。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gxmw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