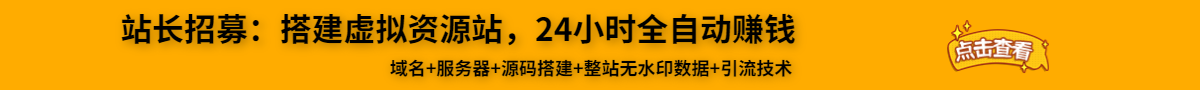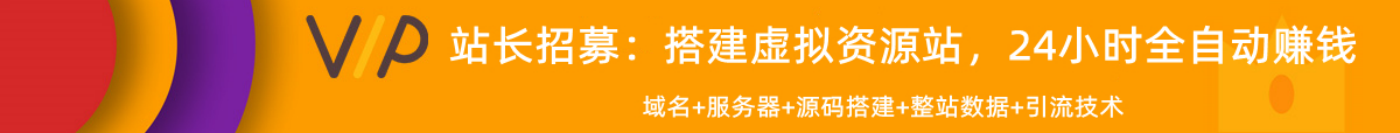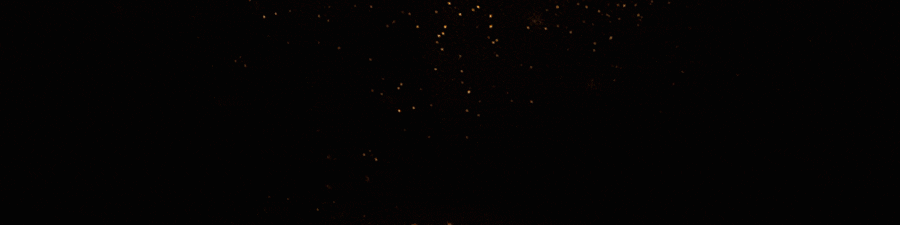维克多 J·布鲁
“我无法保证你一定会爱上相片里的你。但我可以承诺,当你看到我拍的照片或撰写的文字时,你永远不会说‘事情并非如此’。”
作为战地摄影记者,维克多 J·布鲁(Victor J. Blue)曾在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阿富汗出色完成拍摄任务,最近他还在摩苏尔战役中被派遣至伊拉克特警队执行任务。此外,他还曾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纪事报》(The Record)的摄影师。他的照片曾发表在《纽约时报》《纽约客》《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探索频道》上。
PDN:当你报道某位拍摄对象,或希望步入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时,你会尝试建立何种关系?你会告诉他们你将如何使用这些照片、给予他们报酬吗?
维克多 J·布鲁:我试图建立某种透明和信任的关系。我会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要做什么以及我会用这些照片做什么——这些照片将在一家大型报纸或杂志上出版,会在互联网上传播,而你的名字也会出现在照片上。
现在,我不想让任何人受到伤害,我不希望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但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了坏事,我想告诉全世界事情的本来面目及它对你的影响。
目前我无法保证我来了问题就会解决。但如果你让我与你同在,至少有人会知道你正在经历些什么。如果你今天计划做一件十分可怕的事,那么你就犯了大错,因为我会将此昭告天下。我知道被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或听着相机对着自己咔嚓咔嚓响感觉很怪,但你会习以为常。
我无法保证你一定会爱上相片里的你,但我可以承诺,当你看到我拍的照片或撰写的文字时,你永远不会说“事情并非如此”。
PDN: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吗?
维克多 J·布鲁:我永远独立,但永不中立。我试图站在任何一位被摄对象的立场——一位无家可归者、一位因某种不可控力量而遭打击者的立场上……我不屈从根深蒂固的利益、预先确定的结果或毋庸置疑的正统观念。
“我不是政府的宣传者,也不是企业的同伙”,这话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难,特别是当你需要控制自己的政治偏见,并在调查时将它们抛之脑后时。有时摄影师会使用新闻摄影媒介作为推动其政治信仰的工具。我认为,这种宣传工作会在某个领域有用武之地,但一定不是在新闻界。
我明白,摄影师都希望用他们的照片“制造变化”,但这意味着什么?通常,这就是推进左倾政策目标的缩影。我不认为这是大多数摄影师们口中的“改变”。我不想制造变化。我只是希望人们无法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你看到我的故事后丝毫不为所动——你还像以前一样投票、花钱、对待社区的其他人,这没关系,但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事实。
当然,有时你必须站在侵略者的角度报道故事。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需要努力做到不褒奖、不谴责,并帮助读者了解你所看到的。
我绝不是故事的主角。如果你为了得到有趣的图片而移动物体或操纵情境职业操守什么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已经越线了,成了一名表演者。
PDN:拍摄对象曾要求你做过哪些事情?你如何回应他们的要求?你认为哪些事情是道德的?
维克多 J·布鲁:大部分是很典型的要求,食物、搭车等等,也有些要求很奇怪。我试图让他们明白,我来这里不是送礼物的,但我很容易相处。
有时我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午餐,但我不会买一大堆杂货,我不认为这是笔交易;我可能会让某人搭短途顺风车,但我不会刻意捎他们去赴约;我不会购买毒品,也不会将他们从监狱中保释出来……我认为符合道德的方法是竭尽全力不干预故事的本来面目,不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名表演者。因为这不公平。
这世上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与我的拍摄对象境遇相似。有时摄影师倾向接近他们的拍摄对象,这让上述问题更难把控。充当天使深入其中,并利用某种途径帮助拍摄对象摆脱现有境遇毫无意义,这是“白人救世主”心态中最糟糕的一种。
如果你花很多时间与深陷危难的人相处,你应该诚实地展现事实。这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冷血的混蛋,只会让你更专业。
除非爆发危机或生死攸关,否则我是不会出手干预的。当我看到人们严重受伤时,有时我仍会继续拍照,但有时也会停下来施以援手。有时你必须暂时忽略你作为一名记者的职责,承担起你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担当。关键在于我是否是现场唯一能提供帮助的人。我要再次强调,除非迫不得已且你必须担起责任时,不要成为某个场景中的演员。
◇金伯利·布莱德肖。她的父亲布鲁斯·汉森失踪后死亡,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但家人并不知道他的死讯。摄影/维克多 J·布鲁
PDN:最重要或最不能妥协的新闻摄影道德准则是什么?
维克多 J·布鲁:你不能对照片进行处理,添加或删除某些事物,也不得刻意安排拍摄场景。
PDN:你是在哪里学习新闻摄影道德标准的?
维克多 J·布鲁:我刚开始拍摄时,拍摄对象都是好朋友。当他们对着相机摆造型时,我会感到厌恶,此时我会停下来等他们恢复自然后抓拍,我觉得这样更真实。
后来有人向我详细阐述了新闻摄影道德与工作方式,并帮助我充分理解了它们,其中一位就是《旧金山纪事报》和《连线》杂志的吉姆·梅里(Jim Merithew)。他讲述了他所在报社一位图片编辑的故事:如果你到某人家中拍摄,那家人穿戴整齐地迎接你,那么此时你应该离开。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将镜头对准那些为了拍摄而打扮一新的人。
另一位是美联社前摄影总监圣地亚哥·里昂(Santiago Lyon)。当我参加埃迪·亚当斯摄影工作坊(Eddie Adams Workshop)时,他探讨了美联社是如何竭尽全力消除伪造照片的。正是他帮助我清楚地意识到摄影行业的可信度是如何受损的。
然后就是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师协会(NPPA)的道德准则和荷赛的新章程,我认为后者的出台为时已晚,但我喜欢在提交参赛申请时签署相关文件,这让你意识到比赛是有标准的。
PDN:你觉得新闻摄影的道德准则是否已改变?
维克多 J·布鲁:我认为这些年存在某种放松道德准绳的倾向。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大声呼吁全新的摄影方式,将某些人视为“约束”的条条框框抛诸脑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事实信息概念饱受攻击的时代。
这并不抽象,也并非说教。如果你认真工作,你的信誉就是你用来交易的货币。新闻摄影道德准则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这种信誉,它能在现世产生影响。
我们讲述动荡、权力、金钱和政治对人的影响。我们的信誉是读者用来评估我们是否配得上“信使”这一美名的标准职业操守什么意思,破坏这一标准是极不负责的。
PDN:你认为迫使道德观念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维克多 J·布鲁:这并不复杂,因为想通过捷径让照片“脱颖而出”。有时摄影师会通过以往为人们不耻的方式拍摄“伟大的照片”,这就是走捷径。
我宁愿在纪律和道德准则的约束下诚实拍照,即使我的摄影作品未被冠以“伟大”这一称号。我宁愿看平凡的作品,也绝不染指不诚实的摄影。
你不会看到大批摄影师背离道德,只会看到他们在试图改变规则。他们依然希望自己被称作摄影记者,或至少是纪实摄影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艺术”摄影师呢?因为他们依然希望,人们认为他们的拍摄是真实可靠的。
上述观点不会引发人们对“纪实拍摄就应该一成不变”的讨论。旧模式几乎已过时——它将女性、发展中国家及少数民族摄影师挡在门外,为主导叙事服务。
现在,我们正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接纳新的声音,而这只会让这一行业不断变强。许多新的力量正创造成果,他们竭尽全力维护的信誉不应被那些感到“被约束”的同事破坏。
PDN:当出版商获得一个你自费制作的故事时,你遵循的透明度规则是什么?从道德层面讲,你认为自己有义务披露何种类型的信息?
维克多 J·布鲁:我在所有工作中都遵循同样的透明度规则。有时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会出现需要我保持沉默的对话或情形;但当这一情况不存在时,我认为从道德层面上讲,我有义务披露任何事。
PDN:现在,没有非政府组织的物质支持、政府的许可或其他审查实体的帮助与配合,摄影记者往往无法探知故事的真相。你受这些的干扰有多重?摄影师和出版社还应做些什么来提高自身的透明度?
维克多 J·布鲁:这是一个大问题,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必须从容应对的。通常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干扰——战士们理解你到这里的原因,如果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留在前线,他们会尊重你的决定且几乎不会干扰你的工作。
我从未被任何机构审查。这需要技巧,而且我们必须对自己实事求是:我能在这里看到故事真相吗?是否存在阻碍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因素?如果存在,我们只能离开。
令我担忧的是,非政府组织往往是我们报道大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也许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我有很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经验,他们尊重我的工作,不会干涉我,但我也遇到过被他们阻挠的情况。
幸运的是,我成功绕过这一障碍并报道了我知道的全部故事,但这真的是个难题。我认为我们在应对非政府组织时应据理力争,尽量不要加入他们的团队。
大卫·古滕费尔德
“我思想开明,但不会宽恕打破铁律、损害我信誉的人,他们必须出局。”
大卫·古滕费尔德(David Guttenfelder)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撰稿人。他在美联社工作期间曾被派往内罗毕、阿比让、新德里和东京,并在2011年帮助美联社设立驻朝鲜分社。离开美联社后,他的广告摄影作品获得戛纳国际创意节(Cannes Lion Festival)、英国设计与艺术指导协会(D&AD)等颁发的奖项。
PDN:你认为摄影伦理或摄影记者的职责是否发生了变化?
大卫·古滕费尔德:摄影界的变化贯穿我整个职业生涯。我曾在新闻学院学习法律和伦理,为报社工作,然后供职美联社。在我看来新闻是某种呼吁,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编辑室正在招募具备数字媒体或设计技能的年轻人担任图片编辑。很多新入行的记者可能没有上过法律或伦理课,从未在新闻编辑室工作过,身边也没有模范榜样可供借鉴。
现在你审视社交媒体时会发现,虽然Instagram上有7亿注册会员,但受过培训的摄影记者却屈指可数,每天都有人张贴可被视作新闻的照片。
我在美联社看到我的一些旧档案照片曾被用在不相干的新闻里:日本一条谋杀案配了我15年前拍摄的一张犯罪现场照片。
但同时事情也在不断发展,而且我本人对个性化的新闻摄影和不同的故事讲解方式都持开放态度。我希望遇见以全新方式讲故事的摄影记者。
我已经在改变了。当我为报社和美联社工作时,我严格恪守工作单位制定的道德准则。这意味着我甚至没把我的政治观点放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我也不能从事宣传工作或与任何品牌合作。
但我对宣传或品牌合作持欢迎态度,因为我现在在为自己工作,我可以自己做决定。我曾与一家广告代理机构合作开展了一次有关退伍军人自杀的报道活动。我可以成为一名故事讲述者和记者,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份报纸或某本杂志做事。
PDN:对于摄影记者介入故事拍摄过程,或为拍摄对象提供某种东西的做法,你有何感想?
大卫·古滕费尔德:当我为美联社或报社工作时,我的做法始终是,我对“故事”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由于我是独立的,我会开诚布公地展现自己的观点。我会表明我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并说明自己的意见,然后坚定维护它。
PDN:你认为你对读者足够坦诚吗?
大卫·古滕费尔德:当你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工作时,这实际上是一种优势,它让你完全透明,开诚布公地说出你今天的感受。如果我与某人在Instagram上合作,特别是当涉及赞助内容时,我肯定会说“#ad”,并清楚说明这是什么意思,由谁来支付账单,为什么我要与他们合作,以便人们能理解。
PDN:你如何控制拍摄对象对你的期待?
大卫·古滕费尔德:每次你都必须考虑每个人。我会告诉他们:我正在为美联社工作;我们和很多报社都有联系,很多人能看到这些照片;我无法控制这些照片是否能上头条;有时图片会被裁剪或附上说明文字;我的公司绝不会将这些照片出售用于商业用途;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而我要用照片记录下来;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拍摄发生的一切,因为你们希望整个世界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且没有人想粉饰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曾在朝鲜工作过,这是一个“摄影记者”等同于“为国家工作的宣传者,描绘着某种被无害化处理过的乌托邦式愿景”的国家。我来了,还带来了某种提出独立批判观点的传统。
当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会展现一系列看起来十分陈旧或破败的东西?”我会说,“这就是生活的现实。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努力奋斗中,且被镜头记录下来。这是现实,它能促成理解,创造纽带”。
◇金氏崇拜下的朝鲜生活,2016荷赛奖长期项目类组照三等奖。摄影/大卫·古滕费尔德(横划查看更多图片)
PDN:人们对战地记者及他们为政府官员工作这一事实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摄影师对政府官员负有责任,因此会站在他们那边。
大卫·古滕费尔德:我想说,你和谁一起生活,就会逐渐理解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理解或同情。其实这很好,我们实际上很无知。我想让一名摄影记者尽可能地与拍摄对象建立亲密关系,特别是与一个被我们视为“异族”或“敌人”的拍摄对象。
如果一名摄影师在接近他们时可以恪守道德准则,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那么就可以这么做。另一种方法就是干脆把门关上。
有时我在Instagram上分享的作品会使我所做的其他工作黯然失色,美国人消费新闻的方式已经改变。
我在Instagram的作品会收到类似评论,“这是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这是主流媒体,信不得;还是看看这家伙在朝鲜用Instagram发布的东西吧,完全没有经过加工”。
他们认为这是具颠覆性和真实的,但当他们看到另一条同样的新闻时,态度却迥然不同:这是受主流操控的,它不真实。其实两者出自一人之手,拍摄的也是同一件事,只是为杂志提供的图片是我用35毫米相机拍摄的,而在Instagram上分享的是我用手机拍摄的。
PDN:现在,人们对媒体普遍存在怀疑和偏见。人们如何看待不干预拍摄对象或与拍摄对象保持距离?
大卫·古滕费尔德:我有足够的经验,我知道我的独立性何时会受到影响,我作品的可信度何时会遭受破坏。此时我会选择放弃。我不会拍摄一个有关跨国公司影响环境的故事,然后再让他们用钱摆平我。
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雇记者时,会向他们解释一些规定。我会告诉他们:只要你对我诚实,我就会永远维护你;但如果你对我说谎,我就无法保护你。摄影蕴含着巨大的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愿意接受新技术。达妮拉·泽尔曼(Daniella Zalcman)的作品将第一民族人物肖像和景观图像结合在一起,我可以接受。她出于某种原因把图片摆在一起,但这其中根本不存在欺骗。
我思想开明,但不会宽恕打破铁律、损害我信誉的人,他们必须出局。
艾德·卡什
“新闻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视觉报道和故事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影响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一些问题。”
艾德·卡什(Ed Kashi)是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曾为《国家地理》《人权观察》、《时代周刊》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等机构工作。他是VII图片社成员,是非营利组织“说话的眼睛”传媒公司(Talking Eyes Media)联合创始人。
PDN:当你第一次与潜在拍摄对象建立联系,或寻求进入他们家庭和私人生活时,你试图建立何种关系?
艾德·卡什:这取决于故事或项目的性质。如果我正寻求建立某种深刻的亲密关系,且拍摄对象的故事发生在他们家庭内部,那么我会尽可能花更多时间待在他们家中。我从一开始就会澄清我的需求,并向他们明确说明我会尊重他们的底线。
但有些原则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会努力接近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学会巧妙处理这些情况,在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更尊重他们的隐私。
这种做法有时很管用,但有时又困难重重。特别是处于其他文化环境时,一些文化包含的传统或宗教规范使这种访问私人空间的做法显得非常奇怪且不可接受。
因此,保持一定距离很重要,因为摄影师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很不自然,但你如果有这种意识且清楚界限在哪儿,你就可以使它成为一次美好的体验。有些拍摄对象很开放,我就会摒弃正式的方法转而建立某种更轻松友好的关系。
PDN:当拍摄对象暗示你或明确问你“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如何回应?
艾德·卡什:幸运的是此前这种情况并不多,我只在必要时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试着说实话。但的确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拍摄难民和穷人时,这是最具挑战的时刻。
当我遭此诘难时,我始终清楚我是谁、我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我要实现什么。我大多数时候的目标是以某种方式使他们受益——要么讲述他们的故事,要么赋予他们发言权,要么呼吁他们提高意识,要么积极提出帮他们摆脱困境或解决问题的方案。
◇被现代化遗忘的人们:印度公路行纪。摄影/艾德·卡什(横划查看更多图片)
PDN:拍摄对象会要求你回报他们吗?他们曾要求你做过怎样的事情?
艾德·卡什:多年来,我的拍摄对象曾要求我做过很多事情,从结婚到办护照,到办美国签证,再到提供钱、食物、衣物、交通工具等等。
但我只在一种情况下才会施以援手,那就是给予食物、交通和时不时的陪伴。也有几次我给了钱,但这令我很不舒服。
PDN:拍摄一个故事时,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吗?你的目标是“客观”吗?
艾德·卡什:这取决于我的故事和目标。客观是保持开放的一种方式,仔细倾听,不相信某些预定的概念,这些至关重要。
然而我发现这世上有太多问题和不公,找到某种方式来清楚展现它们,这是一个指导性原则。正如我之前所说,新闻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而视觉报道和故事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影响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一些问题。
PDN:当拍摄对象要求你为他们做什么时,你是如何回应的?
艾德·卡什:我会根据拍摄对象及故事的需要做决定。他们为了我的需求调整了生活,完全不理他们,显得麻木不仁,也很愚蠢,因为这样一来你很难与他们建立更强大的信任和合作纽带。
无论人们说什么,与拍摄对象共事都是一种合作。他们可能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或熟人,所以冷漠、冷静地对待他们不是我的做法。
PDN:你有没有觉察到摄影记者与拍摄对象设定界限的方式存在代际差异?
艾德·卡什:有个这样的故事:2004年我在巴格达,在美军袭击后的一个清晨,我们一行人前往萨德尔市拍摄一个停尸房,停尸房里有很多死去的孩子。我看着这些孩子开始流泪哽咽。年轻摄影师觉得我很奇怪,他们也许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拍摄机会。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场面所蕴含的能量与机遇,但萨德尔市受袭击人民的死亡、悲伤与愤怒让我为之战栗。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代际差异或年龄和成熟度的问题。
PDN:你会和学生谈论与拍摄对象的边界问题吗?
艾德·卡什:我会谈及尊重拍摄对象并维护其尊严,了解我们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必须如何行事。
沈绮颖
“我从来不会说自己可以帮他们改变生活,我时常提醒年轻记者不要这样做。因为你承载着他们的希望,这实际上是一种狡诈的剥削。”
沈绮颖(Sim Chi Yin)的新闻摄影生涯从新加坡《海峡时报》担任驻外记者开始,她曾担任马格南基金会人权研究员,目前是VII图片社成员。她的照片和多媒体作品曾在《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世界报》和《纽约客》上发表。
PDN:你如何看待新闻摄影道德准则?
沈绮颖:道德很重要,特别是对一个相对封闭及没有新闻教育传统的地方而言。我曾工作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学生即使远程上课或参与研讨会,也会困惑自己是否可以发表言论。
PDN:当你试图向某人解释你为什么想采访他时,你会怎么说?
沈绮颖:其实你很难向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解释一个纪实摄影师能做什么,及为什么要做这些。
在拍摄何全贵(一位不幸罹患肺结核矽肺病的前采金人)时,我用了好几个月才让他理解我为什么要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我的意图是什么,而他的作用又是什么。当时他的妻子认为,我和大多数只停留一两个小时的记者没什么两样。
我对他说我想捕捉他的自然生存状态,直至生命终结的那一刻。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中国最严重的职业病,我们需要让这个故事强大、动人。即使我不能帮助他和他的家人,也能帮到中国和他一样不幸罹患此病的人。
从新闻摄影过渡到纪实摄影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两者的道德标准略有不同。当我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工作时,我从第一天起就被灌输客观性原则。你应该具备这样的客观性。
但当我开始拍摄长纪实专题,尤其是矽肺病人的故事时,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客观性根本就不存在。
我对某些事情慷慨激昂,因此选择深入挖掘。事实上,中国有600万到1000万人罹患矽肺,我对此并不客观。我不努力展现客观,我要的是公平。
PDN:你告诉他这些照片可能会帮助他或其他人?
沈绮颖:我从来不会说自己可以帮他们改变生活。我时常提醒年轻记者不要这样做。因为你承载着他们的希望,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狡诈的剥削。
在拍摄过程早期,我完全介入其中。从视觉层面上看,这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他已病入沉疴,做不了太多的事情,所以在视觉上缺乏戏剧性的冲击力。于是,我将故事搁置了六个月。
然后,在一个清晨我的手机响了。他的妻子啜涕着说,“他快要死了,你必须帮帮他。”
我主动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筹集了手术需要的资金并将钱直接汇入医院。我匆忙飞到他那里。整整一周我都待在医院,是他的第二个看护人,为他们买了所有的饭菜。
当然,我们之前的关系也完全变了。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我与他及他家人的关系上看,这个故事在这个星期真的发生了改变。因为在他们心中,我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他们认为我救了他的命。
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摄影记者。作为纪实摄影师,我们探讨着通过某个问题来引发社会变革。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而你却选择袖手旁观,那是不合情理的。为什么这个故事完结了,你就要离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完全没有意义,我做了必要和顺理成章的事。当然,我也完全介入了他们的生活。
———END———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Lgxmw666